
《陪伴复旦半世纪》
因为家父是复旦留校教师,所以我一出生就注定与复旦有缘,以至数十年的生活离不开复旦校园。从1966年出生到五十多岁后搬出,整整跨越了半个多世纪。想想自己每个年龄段都会有些无法磨灭的复旦记忆,自称半个复旦人也不为过。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大概五六岁的样子,某个过年前后的严冬,父亲同事见我们全家难得在复旦教工宿舍团聚,因为很多时间还在近郊外公外婆家住,提议要为我们去复旦校园拍照留念。当时复旦校园是个景观,在四周围都是农田的环境下显得尤为明显,除了校外的那幢苏步青洋房楼。那个年代一般拍照都去照相馆,私人拥有个相机还是很稀奇的,虽然拍黑白,但绝对称得上奢侈,有拍照机会算得上是一种待遇了。
出门前,父母关照胸前要别个像章,床底下有个铝制饭盒里放着大大小小许多毛主席像章,有圆、长方的各种各样,有些是别在手帕上的,拿出来后大家自己挑选其中一个,分别别到胸前,虽是简单朴素但很有仪式感,如同过年般喜庆。进到校园里那座高大的毛主席塑像是复旦代表性地标,其正对大学正门,庄严肃穆,是来复旦参观、读书的人们拍照留念的保留节目。
因当时政策我户口在农村,郊区读完小学后附近没什么初中可以深造,很多同学选择辍学了,恰巧那年复旦刚成立职工子弟学校初中,是解决教工子女读书问题,因为复旦小学是早就有的,却没有初中阶段的衔接。于是也就有了到复旦子中借读的机会。学校初建时也就是复旦附中对面食堂后的一间小平房,老师是由复旦附中选派的临时兼职。首届一个年级一个班,完全依靠复旦附中的教学资源,如老师、大教室、图书馆、操场等。到第二届时就扩张了两个班级,边上自然也扩建了几间教室,包括一间固定教师办公室,算从此拥有了专职老师。年轻教师由复旦毕业生补充,而老教师则大多是关系户充当。我过来借读在时间上很是尴尬,第二学期将结束,也就复习一个星期接着准备期末考试了,结果学习跟不上自然降到第二届初一去了。当然这种情况是有思想准备的,没有任何遗憾。由此我也正好读了个完整的三年初中,但毕业之后由于户口等原因还是到别处去求学了。
相辉堂是复旦大礼堂,一般作大型报告会、演讲演出活动使用,当年美国总统里根访华来复旦演讲也是在这里举行的,我和同学为一睹风采紧随总统团队跟着跑了很长一段路,直到他们全都消失在相辉堂里面才作罢。
相辉堂每逢周末都有电影放映,在北面有个单独房间开的窗口是专卖门票,小黑板上会粉笔写着最新的电影节目预告。礼堂里面的凳子是长条,有编号,三列三十排左右。记得第一排和最后排是最差位置,都是人家选剩下的。看过的电影有《佐罗》、《乡情》《黑蜻蜓》《小花》等,至今历历在目。
我大学毕业后在第二师范学校、上海大学文学院授课,之后机缘巧合考入了复旦哲学系硕士学位班两年制,又重新回到了学生时代,穿梭于各个教学楼。第一年是全脱产,科目多,考试多;最后一年基本上泡在复旦图书馆查阅资料,为写毕业论文作准备。那段时间确实静下心来写出了不少学术论文和杂文,也顺利地加入了中国哲学史学会和上海市美学学会,俨然以学者自居,有点可笑。
后来复旦随着时代步伐也开始了扩张,合并原上海轻专的校园,又在上海的很多角落都有校区,还合并医学院,系的建制也提升到了学院建制,看起来规模越来越庞大,但感觉不到原来老复旦的面貌了。
当年南京大学的校长曾提到,一杯牛奶和一杯水的合并,最终会导致稀释牛奶的结果。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许多行业都在追求合并组合,但也有只注重表面上的虚假繁荣,看似一个比一个地“牛”,却像是注了“水”,成了“水牛”而已。
如今快进入耳顺之年的我,搬离复旦也有多年,曾经熟悉的环境已变得越来越陌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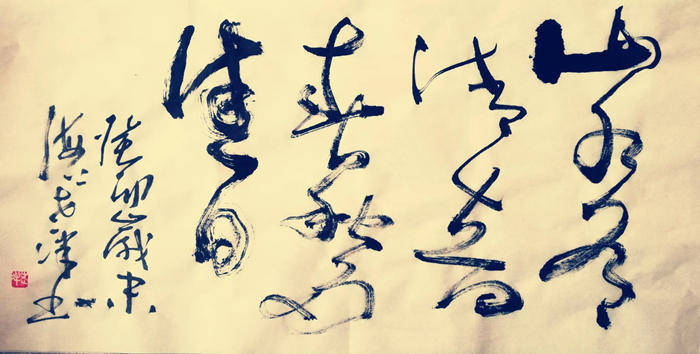
《复旦寓所三迁》
自古孟母有“三迁”之说,我寓居复旦亦有“三迁”经历。回望过去,虽早已时过境迁,但生活场景仍历历在目。复旦在过去的五角场地区一直是独立的存在,犹如独立王国,复旦正门口在有轨“当当车”年代就有了站头,终点站是五角场。
复旦教工宿舍在校外,分布于国年路、国权路、国顺路上,说是宿舍实际上是教工独立分配房,告别校内集体宿舍生活的开始。离复旦校园最近的是国年路上的第八宿舍,三排四层楼房,都是大单间,一般是脱离单身生活的职工房,是复旦分房制度的起步阶段。房间虽大但厨卫在公共区域合用,泡开水的“老虎灶”在中间楼的低下。宿舍对面是工会、中灶食堂和操场,生活极其方便,我们食堂晚饭后会去工会职工之家阅览室看看报刊杂志,然后操场上走走,父亲每次会碰到许多同事,然后聊天、散步,如果碰到周末还会再去校园大礼堂看电影。
在国家恢复职称评审制度后,父亲评上了副教授,最大的改变就是房子得到改观,分到稍远点的第一宿舍,这里的房子是一室半居所,煤卫独立。因长年主要是我和父亲居住,于是小间归我,有了自己的个人空间。这个宿舍原则上属于双职工或一方是副教授才够条件分到,但真正排队分配时往往还是倾向普通职工多点,所以我们已很满足,在工人阶级主流的年代,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还是属于夹起尾巴做人,优越感并不明显,这种思想的影响毕竟随着惯性思维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家父晋升教授后,也正好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全家户口得以“农转非”,房子待遇也变成三居室,是第十宿舍新盖的楼房,在国顺路上,这个住房条件在当时的上海住房极其紧张情况下还是属于非常优厚的了。这是我经历的第二次搬迁,由于自己的粗心大意还弄丢了很多新近创作的画作,想想真是遗憾。
后来突然发现隔条小马路的第十一宿舍旁在大兴土木,据说是要盖新楼,名曰“博导楼”,也就是名义上为贡献突出的博士生导师盖的,所以我们家里也就自然而然地幻想着这次福利的快点到来。但眼看着盖好了,公布分配名单时有点失望,有限的四室两厅房源促使很多人有了想法,时代变了,部分领导近水楼台先得月也在情理之中,剩下的可以到偏僻些的复旦凉城区域享受“博导楼”。
由于父母过分依恋复旦本部这个早已习惯生活的校园环境,毅然放弃迁出,宁可拿一室半的增配房补贴。这个小房后来成了我的婚房,在复旦凉城,但实际上去得不多,大多数时间还是与父母一起居住复旦的老三室里。
(作者:老冸,原名潘志明。现上海市高等教育学会文艺专委会学术委员兼《老冸识趣》主笔。)

Copyright © 2013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哈尔滨资讯网